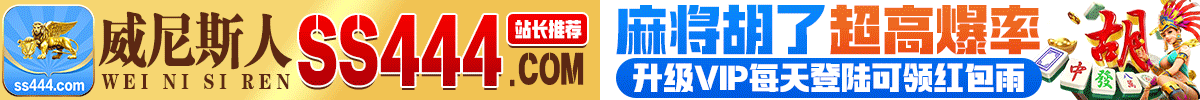第83节(1 / 1)
……
她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坐了多久。直到亚麻纱帘外头的天蒙蒙泛着白,胃里一阵空空的抽搐,全身都出了一层汗。直到阿妈来做饭了,她仍旧有些精神恍惚。
大约是谢择益从前特意交待过,阿妈进来见她醒着,旁边还躺着个小肉团子,稍稍吃了一惊,倒也没有多嘴多舌的打听,径直去到厨房里做饭去了。
她仰头盯着走廊顶头的铜制电话机,她突然想起了某天接通电话时,转接员说过的一个四位电话号码。
上海赫赫有名的名医世家许家,女儿曾留学日本……
她猛的一惊,从沙发里支起身子,将皮质沙发整个震的动了一动。沙发上躺着的小孩揉了揉眼睛,睡眼惺忪的看她。
她揉揉小孩儿的发梢——昨晚已经给他绞过一次了。虽然实在不大好看,总比滋生跳蚤的好。把他圈到电话里下头,她毫不犹豫拨通了许家号码。
要撸小说网 www.YaoLuxs.com
转接过去费了些时间,仿佛是许家管家的人接通了电话;虽然时间很早,听说是许小姐朋友,料到是急事,便也没有迟疑的去叫了小姐来听电话。
许小姐声音倒是十分精神:“喂,林小姐?”
“许小姐早。”她也懒得讲些客套的废话,“我记得你一直想要让人们都知道他们没什么用,对么?”
许小姐显然来了精神:“怎么了?”
她接着问:“我想请问一下,许小姐留学日本时,修的是什么学科?”
“自然是学医。怎么了?”
“嗯。听说过shiro bomb么?”她并非病理细菌学专业,对于这些名词的诞生年月有些不是特别确定。
“我只知道京都大学医学系的石井教授。那是什么?”
她想了想,又问:“那,伤寒沙门杆菌、cholera bacteria、bentonite……和ape呢?”
那头沉默了好长时间。许小姐问:“你从哪里听来这些名词的?”
“我这里有个两岁小男孩,”她将小男孩拉得离电话机更近了些,小声问他几句话。得到回应后,她将电话机拿到耳边:“能听懂他讲话么?”
“嗯……大略听得懂,兴许是南通县的。”许小姐语气明显有些急促:“你在哪里?”
“你知道我家地址的。恭候大驾。”
——
从槟榔屿到上海这一趟旅程,若是乘坐普通邮轮,需要四五日;这一艘轻巡洋舰仅需四十小时。
这一船士兵,不论兵种,多为下级兵。过半数的下尉,两名中尉,只谢择益一个上尉。海上日已落下去,远处鲸鱼在余晖里喷着水汽。旅途余下最后十小时,英国兵们都抓紧时间享受这最后的狂欢,将晚餐从船舱内吃到甲板上,唱片机也搬了出来;音乐、美酒、热带水果与烤肉一应尽有,士兵们尚算清醒的跳着舞;对他们而言,若说还缺点什么,那一定是女人。
和甲板上这群人对比鲜明的,是坐在角落里的斯言桑:浅色衬衫外头一件黑马甲,坐在灯光下头,手里捧着本书,显是视力略有些不大好了,故而才微微眯着眼睛在阅读。他这个作派,一眼望去便知道是英式寄宿中学的模范生;根本和谢择益这种导师去学校为他保释却被他拒绝,当场扯掉马甲校服扔在地上扬长而去的学生截然相反。
船上也有不少曾就读于私立中学的军官,他们谈论起那位叫“斯”的中国学生:牛津的固有学生,剑桥的客座学生,在剑桥名气比牛津大,从中学起就三天两头从伦敦去往剑桥,听说因是那位远在中国女友长于作诗,许多年从一而终的写信作诗,只一心为讨得她欢心。
而今斯言桑坐在角落里,安静得过分了些;沐浴在橙光里头,像幅画似的。
常听说中尉一下下级兵爱鬼混。以前不觉得,而今和那中国少年一比,确实放浪形骸得不像话了些。
英国规矩不兴不经人介绍而冒昧的自我介绍,否则视为无礼。
谢择益想了想,仍旧穿过人群走过去,在他旁边坐下来。
斯言桑将书合拢,微笑着等他发话。
他指指合上的书本询问道:“能否一阅?”
“当然,”斯言桑将书递过来,“请随意。”
接过书,封面上写着:madame bovary。翻开一页,密集的法文的书页空白处标满了汉字,原来是在作翻译。
“学业上违拗父亲意思,他封建大家长做惯了,受不得忤逆。派人克扣钱粮,生活一度十分困窘,偶尔只好以翻译谋生。”斯笑着解释道。
书页快速翻过,停留在夹了便签处。书签为界,左侧部分写满了字,右侧还是干净的。作书签的纸张似乎是照片材质,倒是奇特。仔细一看,果真就是照片。
一共四张照片,照片上都是同一个人。主角是一位少女,心不在焉的站在人群里,人群就这么自动被忽略了。前面三张都在东张西望,最后一张注意到了摄影师,眼睛微微睁大,讶异的神情里透露着整个人有些懒懒的迟钝。
照片里的少女并不算的出挑,在照片里好似整个人都发着光,也不知是因为上相,还是拍照的人专诚在她身上花了心思,格外留意到她的小动作,因此才闪闪发光。
这少女谢择益也认得,不过她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。不过那时的她,他也见过。有些过于安静,有些黯淡狡黠。
一边看着,斯言桑在一旁说道:“两年前作别后,竟没想到这两年之中只有这四章照片全作念想。也不知她如今是什么样。谢先生见到过吗?”
“她?”谢择益仰头,叹口气 ,眯起眼笑了, “做起事来随心所欲得让人头疼。非常非常的懒,懒到超过你想象,也因此总以为没人伺候时,她会难以健康的活下去。若是笑了,眼睛弯弯的,嘴角一个梨涡,像只狐狸。但是并不爱笑,除非有事找你商量。”
他当然还看到过她另一类笑容,锋芒毕露的、柔情似水的,光芒万丈的……令他心醉神迷的。谢择益很愿意看到她有求于他的样子,尽管明知所期待的笑容并不是因他而起。
听到开始的部分,斯言桑脸上仍旧笑着的。听着听着,他眼神慢慢变了,略有些不可置信的看向谢择益。
看了一会儿,他说:“谢先生,我听说你的父亲,对于你的婚配对象有着非常严苛的标准,有这回事吗?希望只是谣传。”
谢择益想了想, “确实有这回事,并且也因此与你一样,生活也曾一度陷入窘境。”
“那么如果你的心爱之人不符合令尊的标准,你又能为她做什么?”
谢择益恍惚了一阵,才意识到斯言桑已经在向他发起进攻。他略觉好笑,微笑致问:“如果是你呢?”
“我会为她放弃很多东西,但凡不接受她,敌视轻慢她,世上种种,她厌恶的,或是厌恶她的,我都与之为敌。”斯言桑盯着他说:“那么你呢?”
谢择益却没有直接回答,只说:“假如她所不喜的正是你呢。”
斯言桑一愣。
“你怎么办?”
斯言桑想了想,笑得斩钉截铁:“绝无可能。”
“这世上太多美好珍贵事物。若事事都值得舍弃,倘若有一天连她都失去,指望谁珍视你?如果是我,我不会为她放弃什么,”谢择益垂着眼睑,只能看到一半瞳仁,“不过我不会让任何伤害到她的事情发生。”
而最让他感到愤怒与恐惧的,是觉察她似乎正在寻求什么伤害。只因她是个彻彻底底的、有着满腔着不了调、落不了地的爱国热血的中国人,而她却明明白白的知道,她在受着“治外法权”的庇护。
因此,他最大限度的给予她力所能及的庇护。
驶入海关,舰艇鸣笛声中,几名水兵为庆贺槟榔屿此行顺利圆满开了两瓶香槟。喧哗声里,谢择益说:“到岸了。是否决定要先去见一见三小姐?”
笑闹声、笛声与海浪声中,谢择益被簇拥着洒了一身香槟。舰艇靠岸,楼梯架起来,下头蹬蹬蹬跑上来两名水手打扮的人,手里头拿着印有黢黑皮肤健美教练的健身招纸,冲谢择益开玩笑似的说:“海边健身俱乐部,腹肌,人鱼线,一季度只要一百块!”
“是么?谢谢。不过,”他语气平和,态度却颇为欠扁,“我恰好都有了。”
满船水兵哈哈大笑,有好事者伸手就要扯掉他军装腰带,几有将他衣服裤子一并扒光的架势。
谢择益这一类拒绝品行导师保释、被寄宿学校开除学籍的“坏学生”,与他是截然不同两类人。这一类,他也见过不少。但活成他这样的,却不多。
几名下级水兵拎着他的行李,带他一路前往皇家军舰码头。下到码头上,前头簇拥着谢择益那群军官也终于难得被他打发走了。他衣服被扯开两粒扣子,手里拿着历经千难万险抢回来的腰带,倒也毫不在乎形象,一边走一边系上。四下寻找一番,径直穿过人群走到斯言桑一旁,问道:“是要在码头上打个电话,还是直接去见?”
汴杰明的车开到门口停稳,小跑过来就要替斯言桑拎行李。一见斯言桑,竟难得颇有兴头的调戏道:“ohhhh look! a china boy!”可以当做他在说中国少年,也可以当做在说斯言桑头发乌黑,皮肤细腻得像瓷器一样,整个人气质相当温润如玉。
还不及他回答,码头外头两辆道奇驶了过来,在几人面前停下来。
为首的车上下来个绸布衫褂的中年人,即便上了年纪,也生的气度非凡,举止说不上的气派十足。
一见那人,斯言桑与谢择益动作都滞了一滞。随后斯言桑嘴唇早咬得发白,恭恭敬敬喊道:“父亲,您怎么来了?”
斯应哼笑一声,冷冷道,“我不来,你决定要到何处去?”
谢择益操着夹生的粤普,快速解释道:“刚将邮轮从槟榔屿接回。不然斯老爷以为要将令郎送到哪里去?”
斯应这才略略将他打量一番,语气不甚友好:“斯家的事,就不用旁人操心了吧?”
谢择益道:“斯老爷说的是。该不该操不操心是一回事,操不操得了心又是另一回事。”尔后侧过头,对面色发白斯言桑轻声说道:“看来令尊,似乎也十分严苛,丝毫不输于家父。”
作者有话要说: *只想说的是,二十世纪最可怕的,其实有可能不是战争。
——
*嗯,两个人的爱情与人生态度。
——
*不要问我斯应为什么要来。
——
*下一章会放一章防盗,明天替换掉,字数只多不少……
——
*这周写的有点少,明天多更点。
☆、〇一九 夜十一
两辆车在斯公馆外停下。两父子下了车, 黑着一张脸, 神情同个模子里刻出来的,一语不发进了屋。
门嘭一声关上, 将一干人等关在外头;斯太太牵着言柏近前来, 看看那暴力关拢的门,问道:“这么久没回来, 怎么一回来就闹起生气来了?”
一行人在外头等管家过来开门。近几月来斯家家仆遣散不少, 倒并非如外界所言“斯家败落了”,也仅仅只因斯应本就喜静,不爱一堆人在跟前走来走去, 索性就应了外头闲言碎语,少铺张些, 排场也小写。一些贴身私人的事情, 便都由这位日本太太替他料理妥当。
人们总爱看一些场面上的风光,是以在外人眼里,从二八年起, 斯家就“衰”了。倒也不是不能盛,南方来请过他许多次,都被他一口回绝,只因他斯应这辈子事了一君, 干不了第二家的事。
他冷哼一声:“这两年你以为他在外头吃了许多苦。其实不然,一门心思没在学业上头,成日玩些文人消遣游戏,同激进青年混在一处, 不仅耽误学业,还几度通信受阻,被拒绝出境欧洲。不会来也罢,我当我斯家有个儿子出息了,要在欧洲做起‘白华’来了!”他气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,斯太太忙替他顺口气,这才接着讲下去:“这次能顺利回国,竟还要托租界地上的白华和南京讲和,实在是奇耻大辱!”
这些斯应也没同她讲过。一开始还时常寄信,托友人教托照料长子,后来一年多也没听他提起过。一开始她还以为言桑在欧洲交了女朋友,所以心里头也没家里父亲和弟弟多少位置了,所以一同斯应提起他就气得说不了话,还暗自好笑了好长时间。
到底母子同心。斯太太正想着,言柏仰着脑袋替她说了:“大哥真的没在欧洲交女朋友吗?”
斯太太抿嘴一笑,慌忙将言柏嘴捂住。
老管家开了门,屋里壁炉燃着火,一行人将外衣脱了在客厅坐下。斯应看了眼小儿子,叹了口气,“还惦记着林家那小丫头呢。”
斯太太一愣:“哪一个?”
斯应瞪她一眼,“还能是哪一个?”
“送别林家之前见过一面。那时三姑娘看起来挺不起眼,虽没她姐姐相貌出挑,却叫人难以忘怀,很有些讨人喜欢。如今漂亮些的二姑娘我已不怎么能记得了,三姑娘仍能记得很清楚,”斯太太回想了一阵,“前些时日,林老爷似乎因着什么事大发雷霆,登报扬言要将那丫头逐出林家,还说解除婚约。这事与你商量了没有?”
斯应摇头,显然对此事仍旧耿耿于怀。
斯太太纳罕:“到底为着什么事情?”
“说是在香港念物理学时与她老师不清不楚。实际如何,其后也致电问过教育总长。徐来这人,是经蔡元培举荐赏识的。蔡先生对徐来人品学识有极高赞誉,三次回电报称,徐来此人极看重家庭,绝不会做出这等事。是以仍旧觉得蹊跷:以斯家与林家交情,即便那丫头真的犯了错,改过自新就是了。往后我与你也仍当她是斯家好媳妇。唯一难办就是怕言桑不肯。但如今看来,他是再喜欢那姑娘也没有了,”斯应吁口气,显然是对自己教导出的儿子既欣慰又叹惋,“即便如你我,将三姑娘放在心里头好好掂量,也愿意多方打听,以免因歹人有意为之而使她凭白遭冤枉受委屈。她还这么年少,林兄怎会如此偏听则暗,还专挑最阴损的法子,让这丫头日后都见不了人?难道其中还有别的隐情?”
斯太太皱着眉头想了想,问,“林老爷是否从前有意,想将二姑娘许给言桑?”
斯应摇头,“好几年前去绍兴前,林老爷便提议过。趁着尚未见到林家两个姑娘,我便让言桑先作决断,叫他选定以后,此生绝不敢再叫我知道他改变心意。”说罢又叹口气,“当初一言,哪知竟叫他记了这么多年。”
见丈夫为儿子婚事愁容满面,斯太太不禁又好笑不已。他心疼生气自己儿子,言桑何尝不是和他一个样。他不肯让言桑从文,只因知道斯家个个都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心性,对政治如此,对爱人依旧如此。若非如此,他在发妻亡故后前往日本,她二八芳华,也不至于苦追他十二年才将他打动。斯家如此家大业大,一旦娶了她,便只有她一个,从一而终。
也是知道自己这个性子,在仕途上极易碰壁,他自己是吃够了这苦头,便绝不肯让言桑再去遭这个罪。特意为他选了学风勤恳踏实,远离政治活动的国家去念大学,也为他挑了一门与政治文章无甚关系的学科;又因而今国内文人以笔为刃,是政斗中推动流言拨弄人心最好用的一柄利刃,时常搞一些文人雅士聚餐会,自当自己是“社会的柱子”,也是如今南京打压最盛的一支队伍,故而斯应也无论如何不肯他学文。
↑返回顶部↑